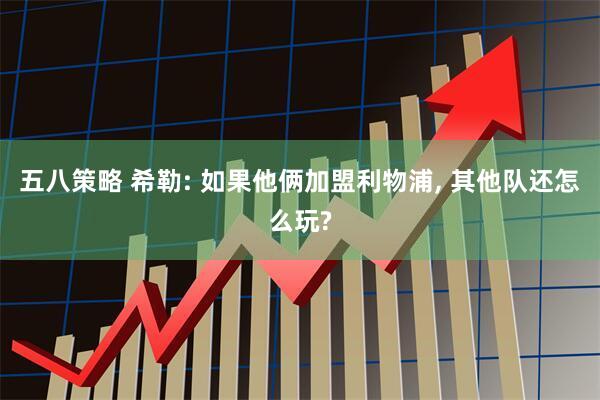“1977年8月22日晚八点,代表同志们请靠右站富盈网,轻声慢行。”警卫员的提醒在灯火通明的天安门广场上显得格外清晰。距毛主席逝世已近一年,纪念堂第一次对少数受邀者打开大门,却没有谁料到,正式意义上的第一批瞻仰者最终是三位刚从海外归来的炎黄子孙。
那天夜色并不深,浓烈的白炽灯把北大厅照得如同白昼。华国锋、叶剑英等人早已在汉白玉坐像前肃立。来自美国的丁肇中、牛满江、何炳棣三人站在代表队伍之后,心绪翻涌。几分钟前,他们递交的“特许请求”被批准,“一定要让他们先进去”——这是中央对科学报国者的一份温情,也让他们意外地成为纪念堂开放前的“第一位来宾”。

镜头先拉回到十一个月前。1976年9月9日凌晨,中南海灯火通宵,华国锋刚与汪东兴敲定保护遗体方案:取苏联列宁墓经验为鉴,却不能全盘照搬。徐静和刘湘屏登上名单,他们需要在15天内完成初步防腐,又要留下二次长久保存的余地。“只许成功”的话语没有再次出现,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分量。之后的六天吊唁,七百万人次涌进人民大会堂,场面至今难以复制。
水晶棺的研制成为另一场隐秘的竞赛。北京玻璃总厂一度把熔炉温度加到2000摄氏度,仍难消除折射影像。有人提议换用光学玻璃,有人坚持纯水晶方案并行。25吨一级水晶、64次实验、上百块报废品堆满厂房角落。直到1977年8月初,通体无暇的六块水晶板终于嵌合成功。从车间到纪念堂南门只不过几公里,却动用了一支摩托车护卫队,还借调了64名解放军小伙子肩扛入场,只因任何机械吊装都被否决——振动系数不达标。

而纪念堂本身,短短十个月拔地而起,更像一次集体意志的凝固。设计组刚成立就被问到“放哪儿合适”。中南海、香山、八宝山,甚至有人提出在井冈山原址立陵,但最后还是回到广场中央。原因很朴素: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此富盈网,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也在此。周恩来早年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——“让这里成为人民最喜爱的地方”。决定拍板那天已是1976年10月8日,秋风透凉,几位首长在城楼上俯瞰广场,谁都没再犹豫。
工期极限只有六个多月。北京当年罕见低温,夜里零下十四五度,混凝土一浇就结冰。施工队在模板外通蒸汽,耗煤量激增,道道白汽让广场宛如雾海。有人从40米塔吊上摔下,仅擦破皮却拒绝去医院;有人三天三夜没合眼,回宿舍倒头睡在水泥地。统计表显示:六个月内绑扎钢筋1.2万吨、挖运土方114万立方米——不亚于再造一个小型人民大会堂。
雕塑创作同样跌宕。北大厅巨型坐像敲定房山汉白玉,三个月完工,速度惊人。真正犯难的是四组群雕。方案会上争论反复,直到有人翻到《毛泽东选集》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那页才豁然贯通——主题就用人民战争与人民建设。于是,从四川到东北,草稿如雪片寄来,最终挑出“秋收起义”“抗日烽火”“土地改革”“时代新貌”四幅。八十多位雕塑家在简易棚里一住半年,最冷的夜里靠烤铁桶取暖,手指僵硬也不肯停锤。

再说回1977年8月22日晚。三位海外科学家在北大厅鞠躬后转入瞻仰厅。透明棺内,毛主席双手覆盖党旗,神情安详。牛满江后来回忆:“那一刻,科学与信仰交汇,心跳声比脚步声更响。”他们缓缓绕行一周,未发一语。紧随其后的,是参加中共十一大的代表们。许多老红军泪流满面,有人恨不得再握主席的手,却只能高举拳头悄声喊一句“报告首长,我来了”。
第三位特殊访客是铁托。8月28日午后,他在李先念陪同下走入大厅,花圈上仅写“南斯拉夫人民敬献”。这位曾在国际舞台与各方斡旋的硬汉,在水晶棺前停留了足足五分钟,随后轻声说了一句塞尔维亚语,大意是“老朋友,我兑现承诺了”。很多工作人员当时还不知道,毛主席生前曾称赞他“骨头是硬的”。

9月9日纪念堂正式对公众开放。首日安保压力空前,广场外围排队长龙五公里。老人拄拐、小孩骑肩,没有人喊累。那之后,每年清明、国庆,总有人专程来北京就为了走这一圈;外国首脑访华,把敬献花圈当作重要政治礼仪;普通游客则在留言簿写下寥寥数句:“没见过主席,但他一直在。”
回望建造过程,它其实是一部“众人成城”的现实史诗。设计师、医生、玻璃工、农民工、警卫员,一个个名字未必载入史册,却在不到十个月里让世界刮目。也正因此,当三位远道而归的华裔学者成为第一批瞻仰者时,象征意义远胜排队次序——毛主席生前常讲“归根结底是人民”,此刻“人民”三个字被再次写得铿锵:不论身处何方,血脉与记忆,终会让我们在同一尊像前默默致敬。
嘉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